彼得
彼得·凯恩今年68岁,他谈过138个女朋友。

莫妮卡
138个女朋友当中,莫妮卡第一个回复我,事实上,无论发给她什么,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她只字未提我的的采访请求,而是顺溜地报了遍自己的简历:普林斯顿本科、哈佛硕士、十年麦肯锡,如今是安永的高级合伙人。我问她下周某时某刻有没有空,她没过两分钟就回复了:“没空,那时我在开会呢。”
这样的对话会重复五六遍,直到她终于答应了我占用她三周之后半小时的宝贵时间——喏,就是她坐公司配车赶去机场的半小时车程。她的秘书马上给我发来日程,并且督促我“尽快确认”。当然,毫无意外的是,就在这确定的半小时来临前的五分钟,她一定会发来一封道歉信:临时有会,改天再约。我能想象到,她的香奈儿高级套装,她郊外的大别墅,她唯唯诺诺的下属,还有,从来没有属于过她的时间。
玛格丽特是个喜欢吃炸薯条的牧师,写了几本灵魂拯救和自我帮助的书。如果你是个有钱的生意人,玛格丽特会向你推销她的灵魂拯救大礼包——从今天开始的三年期课程,给你员工讲宗教信仰和团队建设和赚钱的关系,保证员工死心塌地被洗脑。当然,前提是你付给她一大笔学费。
罗宾在新奥尔良做麻醉师,她最自豪的事情是今年大学毕业的儿子。就像你已经听过的几千个故事一样,这孩子毕业之后准备去纽约和朋友创业。对此,罗宾的评价是,“我们这一代都去当了医生,就像我儿子这一代都去了创业。”
亚罗走进旧金山Mission区的一家印度餐馆,指指肮脏的街道和文刺青的行人,“这个贫民区啊,我是十几年都没来过了!”那天下午她要和丈夫去奥迪专卖店挑选一辆新车,然后奥迪会把簇新的车寄到法国普罗旺斯好让亚罗开着新车乡间旅行。谈起之前的那次婚姻,她有点冷漠,“有些人就是不能一次成功的。”谈起彼得·凯恩,她说她压根记不得彼得·凯恩是谁。她喝了一口马天尼——是的,在这家廉价的印度餐馆,她硬是点了两杯鸡尾酒,又开始讲法国和奥迪车。
高尼是那种……政治正确的说法是……“非常为自己的种族身份感到自豪的人”,也就是说,她平生参加的所有社团都是美籍亚裔小团体——华裔学者协会、华裔精神医生协会、波士顿华裔协会、新英格兰女华裔协会……一个抱团的女人,任何人都会这么说她。不过,换一个角度,美籍华裔这个团体的确缺乏像她这样拼命发声争取权利的人。和美国黑人或者拉丁裔相比,华裔的确显得太安静太不团结。作为一名公共政策教授,高尼的论文课题包括美籍华裔老年妇女的医疗需求、华裔LGBT族裔的心理咨询、华裔家庭抑郁症的遗传因素。
万象凌晨5点,莎拉穿着吊带衫和运动裤奔跑在万象的街道上。她说老挝是一个极端礼貌虔诚的国家,当她穿着黑色长裤长袖出现在万象大学的讲台上教授英语,学生们(从6岁的富二代到60岁的军官)会对她双手合十地鞠躬。而当她穿着吊带和短裤在万象的街道晨跑, 40℃的高温让她汗流浃背,那些虔诚的佛教徒,把合十的双手分开,放肆地在她屁股上打一下,向她吆喝着,“小骚货!”
莎拉说,性别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啊。
还有努雪,一个斯里兰卡美女,为了躲内战而在悉尼度过了幼年。她本来打算在澳洲读大学,结果舅舅寄给她一所美国大学的宣传小册子。小册子里没有怎么讲学校的师资课程,反而讲起了校园建筑里的滴水嘴兽,呃……就是那些墙面上输水管道末梢上的雕饰……努雪想,“在宣传册上讲滴水嘴兽的学校真是奇葩啊!我喜欢。”她是那么那么喜欢这所花整个宣传册用来讲滴水嘴兽的大学,第一年申请被拒她居然第二年继续申。于是,这本滴水嘴兽的招生册成了她本科读建筑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她现在成了建筑系的博士生。
138个女人,我并非个个欣赏,就像初次相识的陌生人一样,彼此之间的友谊和判断全靠缘分。我认识她们的契机是彼得·凯恩。而彼得·凯恩认识这些女人们的契机是1966年11月5日的一场比赛:普林斯顿大学一年一度最盛大的橄榄球赛,普林斯顿主场,哈佛客场。
普林斯顿大胜,大学二年级的彼得回到寝室楼,去自己的隔壁寝室和朋友们庆祝。然后,就像他过去两年的每天重复好多次那样,他没有打开门离开这个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这样需要拿钥匙),而是打开了窗。这两个相邻的三楼房间之间隔着一个装饰性的狭小阳台,两个房间的男生图方便也是为了好玩,总是走出窗外通过这个阳台串门去隔壁寝室。
只是这一次,彼得忘记了自己已经在隔壁寝室而不是自己寝室,他应该往左拐才能踏到这个狭窄的阳台。他一边和朋友谈笑一边下意识地伸脚往右拐。一脚踏空, 二十米的高度坠落,头先着地,送往医院途中死亡。
彼得·凯恩死于1966年11月5日,19岁,普林斯顿大二,从未谈过恋爱。
彼得·凯恩今年68岁,如果他没有死。如果彼得没有死,他将在1969年本科毕业,他将能看到那一年普林斯顿第一回招收本科女生,在大学成立的第223个年头第一回实现了男女合校。
彼得没有看见这一幕。可是,1969年和那之后的每一年的感恩节前夕,大一新生中总有几位幸运的姑娘会收到这样一张纸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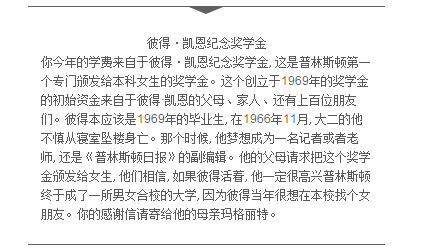
2007年,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打开信箱,奖学金办公室通知我,这一年的所有学费和生活费都来自于这个倒霉的彼得,这个当年很希望男女合校好让他找女朋友的彼得。我站在信箱前面笑出了声,“这不是在给死人找媳妇么?”
真是遇到鬼了。
女友们

四十年过去了,玛格丽特仍然记得大一的那节微积分课。1971年,38个男生,2个女生。老师在黑板上写题,问谁会做。整个课堂一片寂静,大家都被这道题难倒,玛格丽特举起了手,“我会。”全班都转过去看她,眼神是在说:一个女孩子,不可能会微积分。
两年前的1969年,校董会经过多年商讨,终于同意实现普林斯顿本科生的男女合校。为了争取到本来持反对意见的董事,董事会的最终决议是,“在不减少男生招生数量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扩招女生。”玛格丽特入学的1971年,男女合校的第三年,招收男生800人,扩招女生200人。
我笑着问,“四比一的男女比例,是不是女生特别抢手?”我猜想,像彼得那样愿意在学校里找女朋友的男生肯定不少。
玛格丽特说,“你猜是这样。实际上呢,男人们还是更倾向于进口货。”进口货,指的是邻近的女子大学和女子高中里的女孩子。“男生不喜欢普林斯顿的女生,她们太聪明了,我们那届的男生还是习惯于女人处于附属地位,不应该和他们平起平坐。”——直男癌,现在的说法。
玛格丽特在华盛顿州的一个农业小镇长大,家境非常一般。对于全家人都从未去过的普林斯顿,外婆和妈妈的建议是,“大学好好过,嫁一个普林斯顿男生。”
她试着和同校男生约会,然后总结,“他们只适合做朋友。”
她又反思道,“那个时候,女权主义在美国刚刚抬头。如果我真的按照外婆的建议在学校里找个未婚夫,嫁人相夫教子,我也会被其他女生看不起的。”同班的女学生自发组织了讨论会,讨论如何在恶劣的大环境下做个独立女性。大学四年,玛格丽特没有结交富贵子弟,朋友圈子是一起在食堂打工的穷孩子们。
大学时代,她对宗教和数学都有兴趣,职业志向是成为一个牧师。大学毕业,她去俄勒冈州的一所大学做“驻校牧师”,因为没有其他选择,“当时大部分的教堂牧师只招男人,只有大学里的驻校牧师职位接受女牧师。”
大一的微积分课上,玛格丽特的男同学们不相信她能做数学题,而在所有的采访人中,她会是经受学院训练最多的一个。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她还获得了数学硕士学位、神学硕士学位、宗教学博士、宗教学博士后……
直到快40岁了,玛格丽特才结婚,丈夫是麻省理工的研究员,两人决定不要孩子。“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我的职业兴趣,我花了更长的时间找到一个男人愿意支持我的职业自由。”

莎拉
莎拉说,她想念中国。
两年前,她大学毕业,来到上海松江的一个私立双语学校教英文,这是这位加拿大姑娘第一次来到亚洲。一年之后,她转去老挝的万象大学教英文。在上海的那一年,她对中国爱恨交织。My love-hate relationship,她这么说。“可是,当我去了其他的亚洲国家,我越来越感觉到了中国的好。”
中国的好?
“老挝人在公共场合非常礼貌,而中国人非常直接。这种直接,一开始让我感觉粗鲁,可是渐渐的,我喜欢上了它。在中国,大家横冲直撞,因为生活是有奔头的,日新月异。而老挝,什么都没有变化,国家仍然停留在越战留下的伤口里,一切都太忧郁了。我去柬埔寨、去越南,这两个国家已经从越战中恢复了,经济在起步,而老挝呢……万象,慢得根本不像是一个首都。”
她是一个一米八的白人姑娘,很漂亮。早上8点,在Skype那头我看见她穿着吊带运动衫和短裤,她说,刚跑步回来。她说,“我穿成这样是因为今天40℃,不是为了在万象找个老公。可是,老挝男人看着我,指指点点,分明是在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要穿吊带短裤,为什么她要故意弄得满头大汗,她一定是在勾引我们。”
莎拉说,“在中国就不会这样。中国人不会物化我。”物化。这个用词让我吃了一惊。
“在北京上海,人们都很国际化,根本不会多瞧我。在小地方,当然经常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因为他们比较少看见外国人。在黄山,我对着山拍照,发现很多游客在拍我。这都可以理解,大家只是对于外国人很好奇,因为我长得不一样,可是在中国,我从来没有觉得男人是以一种性欲的眼光看我,从来没有不尊重地看我。在老挝,这样的感觉却非常明显。”
莎拉说,虽然她对中国爱恨交织,她其实想念死中国了。
她打算结束了这学期就从老挝返回中国,在清华踏踏实实学习两年中文。
经济上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人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开放,减少了对女性的“物化”,这是莎拉作为外国女子的亲身感受。虽然,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男女收入差距从几乎为零慢慢变大到了2013年的40.7%,为整个亚太地区性别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我
我。
高三申请美国本科,要写一篇自由命题的申请作文,老师说,“随便写,写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写什么好?我写了一个从小接受奥数训练最后拿一等奖的故事,老师说,没有感情。写一个去美国高中交换学习适应新环境的故事,老师说,没有感情。最后,我写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我作为女人的困惑重重。老师说,“很好。不过这篇作文的缺点是没有提供一个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我看着他。
于是几个月之后,当我得知大学第一年的所有费用皆来自这个专为女生设立的奖学金时,这成了一种暗示:在申请这所大学的作文里,我提了一个困难的问题,而大学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提供了一把通往“解决方案”的钥匙。奖学金办公室希望我写给彼得的母亲一封感谢信,并提供了邮政地址。大学刚刚开始两个多月,我整天在担心作业完不成朋友交不到,可是到我下笔,写的却是“亲爱的凯恩太太,我过得很好。”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专业,这学期选的生物课搞得焦头烂额,信里却写,“我对生物学很感兴趣,也许会成为一名医生。”
和大一新生一样,我报名了许多社团,觉得大部分社团都很无聊,写的却是,“国关政策俱乐部真挺有意思的,我以后打算多参与他们的活动。”虽然大一才过了两个月,我和我的同学们却在竞争的压力下已经开始担心找工作的事了,在信里,我却写,“每天都很充实,我也期待能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估计一下,彼得的母亲凯恩太太当时至少八十几岁了。我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要向这位陌生的老太太讲这么多言不由衷的细节,而不是简简单单地写上一句“非常感谢你的捐款”。无法解释,寄出这封谎话连篇的信,在信封背面写上“感恩节快乐”,为何自己突然不再焦虑明天的作业下周的考试。无法解释,为什么没有收到老太太的回信,会让我这么失望。
更无法解释的是,那天之后,八年过去了,本科生活已经过去太久,久到我已经在波士顿开始读研究生,久到连这个研究生学位都只剩下了最后一个学期。八年中有好几百遍,我想起彼得、他的家庭、那场怪异的悲剧,还有,和我一样曾受到他资助的“女友们”。
尤其是这个雪天。学生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刚开学,波士顿的连绵大雪却让整个城市停顿,学校停课,店铺关门,街道上没有车,路人在街上滑起了雪。我窝在家里,突然非常想念彼得,想念这些和我得过同样奖学金的女校友,我们之间似乎形成了某种隐秘的姐妹会。姐妹会中的成员都是彼得的女朋友,陪伴永远年轻的彼得在校园里度过了一整年。
我想认识她们。
于是八年过去了,这个雪天,我突然提笔给普林斯顿奖学金办公室写了一封长信,告诉这个办公室,能联系到这些往届的受益人以及凯恩家族对我来说如何重要。我请求这个办公室提供她们的联系方式给我。彼得的母亲想来已经仙逝了吧,能否给我凯恩家族其他成员的联系方式?
奖学金办公室回复说:很抱歉,我们不能公布这些隐私信息。
线索断了。
过了两天,这个办公室又说:你不如写一封请求信给我,我能帮你转发给这个奖学金的所有138名受益者,有兴趣的人可以主动来联系你。至于这个奖学金的捐助方,很抱歉,我们的确只有彼得母亲的邮政地址,没有电话,没有e-mail,没有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
于是我写了一封e-mail:给138名我不知道名字的姐妹们。
我又写了一封平信,寄给了八年前的同一个平信地址,那个没有给我回信的地址,“给尊敬的凯恩太太,八年前因为你的慷慨捐助我得以入学。”
给尊敬的凯恩太太,但愿你还活着。
好多天过去了,农历大年初一,我和同学在寝室包饺子,突然有个陌生来电。满手饺子馅去接电话,电话那头说你好,我的名字叫安迪·凯恩,是彼得的长兄,我代表我今年99岁的老母亲,她失去了记忆,无法和你沟通。你想来我家吗,康州格林尼治?
彼得
安迪和他的妻子在火车站接我,开车去他在康州格林尼治的别墅。他和我握手,手抖得厉害,耳背,虚弱。他今年78岁了。格林尼治是华尔街银行家安家立业的聚集地,和四周穷奢极欲的豪宅广厦比起来,安迪的小别墅显得过于中产。在华尔街投行干了十年攒够了买这别墅的钱之后,他辞职做了一个公立中学的历史老师。
到家后没多久,电话响了,安迪说,“是彼得。”彼得?是的。幼弟彼得惨死的那天,妻子正怀着头生子。作为纪念,安迪的长子被命名为彼得。安迪的父亲威廉和二弟史蒂芬都在十几年前去世。母亲玛格丽特——也就是我写信去的凯恩太太,今年99岁,住在一个全天护理的养老院里。凯恩太太最近几年因为几次小中风而慢慢丧失了记忆,不太能说话。彼得之后,这个家族再也没有后代去普林斯顿读书。
几周前,安迪像往常一下去养老院拿母亲的账单,在一堆账单里面发现了我的信。安迪说,母亲每年都会收到些来自大一女生的感谢信。有时候,母亲拆开信,没有看懂是什么,自己就扔掉了。有时候,安迪及时赶到,会给她读这些信,然后保存下来。即使是朗读这些信,母亲也不太能听懂。有时候,母亲会问:谁是彼得·凯恩?
就像是置身在一个幽灵之家。

彼得·凯恩
威廉·凯恩1933年从普林斯顿毕业,在华尔街从事金融业,两年后与玛格丽特结婚,生下长子安迪和次子史蒂芬。“二战”爆发,威廉·凯恩服兵役,作为炮兵团一员远赴欧洲战场,军职至少校。“二战”后回国,生下幼子彼得。幼子彼得与长子安迪之间相隔十岁,安迪于彼得,亦兄亦父。
就像当时所有的体面人家一样,威廉把三个儿子悉数送去了最好的私立高中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三个儿子资质迥异,长子安迪成绩糟糕,高二不得不转学去了另一所高中,次子史蒂芬成绩平平,勉强完成了高中学业,然而幼子彼得,哥哥安迪评价说,“是全家的明星,全家的宠儿”,高中阶段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毕业进入了父亲的母校普林斯顿。彼得和自己高中的一帮子哥们儿住在相邻的两个寝室,寝室在三楼,窗外有一个装饰性的小阳台连接。
威廉是普林斯顿的铁杆校友。大学毕业后他做过多年的学校筹款志愿者,每年普林斯顿对决哈佛的橄榄球赛更是每场必到。他观看的最后一场橄榄球赛是1966年11月,幼子彼得当时正在普林斯顿读大二。比赛结束,普林斯顿获胜,和彼得聊了几句家常之后,威廉带着胜利的喜悦和妻子驶回纽约,在途中的一个收费点被拦下,收费站员工说有一个给威廉的紧急电话:威廉的朋友来电告知,彼得刚刚不幸坠楼身亡。
“没有父母能经得起孩子的死。”那之后父亲威廉老是念叨这一句。
大一那年,彼得为John Lindsay的竞选团队做了一年的实习生,Lindsay成功当选为纽约市市长,一干就是八年。彼得的葬礼日,时任纽约市市长的Lindsay给威廉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回忆彼得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孩子。
1969年,普林斯顿男女合校的第一年,经过几年的筹备,威廉向大学捐献了“彼得·凯恩纪念奖学金”的初始资金,规定这个奖学金的唯一条件就是受助人性别女。直到他去世,每一年威廉都会再为这个奖学金捐赠数千美元的个人积蓄。
奖学金的受助人之一亚罗说,“威廉看起来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他是华尔街银行家,他打高尔夫,他的孩子们都读私立高中。这一切都像是一个非常体面非常保守的人会做的事情。所以让我震惊的是,他居然会捐款成立普林斯顿第一个给女生的奖学金,这在当时一定是一件激进的事情,一件不像是体面的人会做的事情,因为当时很多体面人反对男女合校。”
2001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登出了一则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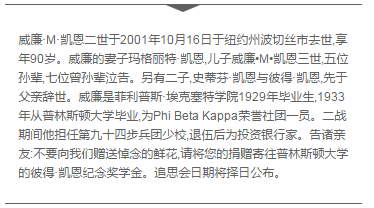
我
对于这个奖学金,安迪知道得很少,“全是父母的决定,没有和我们商量。”这些年来他从未去过问过奖学金的运行情况,只是偶尔从母亲的邮箱里找到些大一女生的感谢信,还有一年一度来自奖学金办公室的报表。我的采访很快就无话可说,除了回忆感叹彼得坠楼的那场悲剧。悲剧发生得太远,说到一些细节,我和安迪都笑了起来。
我问安迪的妻子,大学毕业的她,结婚之后就没有去工作,有否遗憾?
她说,不遗憾,她们那一辈的女人都是这么选择。
问她,生活中有没有碰到过性别歧视?
她说,没有啊,从来都没有感觉到任何歧视。她回答的口气显得很惊异,是我问了一个答案显然的问题。
她反问我,你呢?有没有碰到过性别歧视。
我说,有啊。
她说,比如呢?
我说,我妈难产,生我生了三天三夜。我出生时没有哭,脐带紧紧绕在脖子上,母女都奄奄一息。我爸看到我是女孩,特别失望,扔下我和我妈,在酒馆里醉了三天。
沉默。
我说,如果一个人生命的开头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会是她人生唯一的一个故事。
沉默。
安迪说,我真的很抱歉。
我说,如果一个人的整个童年不断被最亲的人提起这个故事,作为威胁或者玩笑或者仅仅是就事论事,她会倾其一生去忘记,摆脱,重构这个故事。会因为这个故事而自怜自艾,自我厌恶。继而是不断试图回答,女性这个性别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断试图回答,不断失败。
你还好吗?安迪的妻子小心地问我。
我说,上一回我和人讲这件事,是在华尔街的一家投行,大三找暑假实习,面试我的是一个满嘴粗口趾高气扬的中年白人男子,问我为什么想当交易员。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跟他讲,初中住在二十个女生一间的通铺寝室。跟他讲,高中考进市重点的理科实验班,全班四十个男生,八个女生。跟他讲,高一去参加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几天后监考老师打电话到我家,问我是男是女,然后恭喜我得了奖,才知道,女生得一等奖的分数线要比男生低。跟他讲,我已经受够了,女人不能做男人的职业,能像男人一样成为一个交易员。
我说,然后奇迹就发生了,那个趾高气扬的中年白男突然脸涨得通红,他不断和我道歉,不断说真是对不起。当天夜里他给我打电话,恭喜我拿到了这份工作。我说,那是最让我惭愧的性别经验,因为弱势的性别而被同情,而非凭借实力赢得肯定。而现在呢,瞧吧,我又在你面前做了一遍同样的事情。
安迪说,我真的很抱歉。
沉默。
安迪的妻子试探着问,你知道吗,最近一阵子有很多女权运动,“Lean In”,向前一步。你参加过吗,对你有帮助吗?
我说,参加过好多场Lean In。一群穿职业装或者晚礼服的女孩,邀请一个商界或者政界的女强人做演讲,开酒会,酒会上聊指甲、头发、明星。我说,这一点都帮不了我,一点点都帮不了。我觉得那些“技术性”的女性问题——怎样谈恋爱,几岁要孩子,要不要把卵子冻起来——并不是最困扰我的,我也不需要陪我聊指甲和头发的女伴。
我需要解答的是,如何和作为女性的自己相处,如何和这个性别的历史解读相处。一想到这个问题,我仍然惊慌失措。
什么样的事情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我无法控制这个问题,问题自我生长,像野草一样。
我只知道什么样的事情能安慰我。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如说,普林斯顿历史上第一位以正教授的职位被聘用的女人是汉娜·阿伦特,得知这样的事情能安慰我,一想到这个我就非常开心。
嗯,还有什么事呢?
还有今天,能见到你,了解彼得的家庭,今天也是安慰。能认识彼得的女友们,听这些女人讲自己的故事,是极大的安慰。
女友们
“在课堂上,我是唯一的女生。有时候,老师会针对一个话题让大家挨个儿说自己的见解,轮到我发言,我就觉得,无论我说什么,都将代表所有女性的观点。所以我不敢畅所欲言,只讲中规中矩的话,那些女性应该讲的话。如果你处于极端少数,你将自然处于劣势。”罗宾1971年入学普林斯顿一年级,专业是生物,因为她一直以来梦想成为鸟类学家,好好研究世界上的鸟。
“后来,因为一个教授的推荐,我报名了一个去亚马逊观察鸟类的科学考察,是考察队唯一的女生。我发现,科研者们不喜欢在田野旅行的时候有女研究者同行。”于是大学剩下的时间,她忘记了世界上的鸟,生物学专业对于罗宾就意味着待在地下室的实验室里,“养老鼠,杀老鼠,麻醉老鼠。”——不知是否该感谢这段经历,现在她在新奥尔良担任一家医院的麻醉师。
罗宾对她同届男生的看法并不完全负面。“我的确认识些男生,他们歧视女生,反对学校招收女生,不过大部分男生不是这样的。”她和一个同届的男生谈恋爱,最终结婚,毕业后两人都去了医学院。
“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女人想做医生,就必须放弃孩子,一开始十几年的工作实在太累太忙了。现在不一样,环境好了不少,很多年轻的女医生在读书或者住院轮转的时候就生孩子。我们那时候,想都别想。“她感谢同为医生的丈夫对自己的事业很支持,”比我父母支持得多。“每次罗宾为迟迟没有生育而内疚时,她丈夫总说,“你看,你现在太忙了,我们可以等一等。”

罗宾
罗宾24岁结婚,39岁生了第一个孩子,41岁生了第二个孩子。
“我们那个年代,如果女人想做建筑师,就必须放弃孩子。”
吊诡的是,仅仅一天之后,和罗宾几乎同样的话,从比罗宾年轻20岁的娜奥口中说出。娜奥35岁生第一个孩子,因为那一年耶鲁大学给了她的一份教职,让她得以从建筑师事务所的高强度工作中脱身,有空闲时间带孩子。39岁她生了第二个孩子。
从履历上来看,娜奥似乎是一个享受着无限自由和浪漫的人:大学的三个暑假她在南极与物理学家研究南极的冰,她本科的毕业设计是为南极设计一座新研究站,大学毕业她跳上了一艘科研轮船当上了海洋学讲师,她在墨尔本做过雕塑家,在日本和美国各地设计过房子,现在是麻省地区三所大学共同聘任的建筑学助理教授…
可是,在东京的隈研吾建筑都市设计事务所,她发现五十多位设计师中,仅有四位女性。其中两个和她一样,是外国女人。只有一个日籍的女设计师,还因为她研究生在美国读,还因为她还没有结婚。这个事务所其他的女性的员工呢?秘书,前台,助理。
可是,在美国的ABK设计事务所,她上项目和施工方的工程师们开会,整个会议室经常只有她一个女人。好多次开会,施工方的结构工程师有问题,不会直接问她,而是会转过头问她的男性助手,仿佛他是专家,她是助手。因为她怎么可能懂结构工程?因为美国的建筑师,真的能升到管理层的,只有12%的她,和88%的他。
在旧金山这家印度餐馆里,我吃了个饼,亚罗喝了两杯鸡尾酒。她是个丰盈肉感的女人,兴致勃勃地谈论酒精、姐妹会、曲棍球,谈什么都兴高采烈。
9˙11当天雅罗在纽约,在CNN做一档西班牙语美食脱口秀的制片人,并不开心,却得过且过。9˙11改变了所有纽约人的人生,包括亚罗。她从CNN这个不开心的工作辞了职,回到老家波多黎各陪陪父母,等她休假回来她发现9˙11也改变了她丈夫的人生决定:她丈夫想要搬去他魂牵梦绕的得州,她坚决不同意,于是她丈夫说,离婚吧。
Starter Marriage. 亚罗这么称呼自己的第一场婚姻,显得毫不介怀。离婚那年她30岁,第一段婚姻没有孩子。
“孩子吗?离婚那天,我做了个决定,不要太为此紧张。我决定这辈子有没有孩子对我来说没这么大不了。很多女人到了年龄之后荷尔蒙会变,会变得特别特别想要孩子,我不是这样的,我没有感到这种冲动。”
这样的话从她肉感又大大咧咧的嘴里说出,显得再自然不过。我事后听那天的录音,却明显听出了语气中的逞强。
她复习考试,然后进了法学院读书,读书期间与现在的丈夫相识并闪电结婚:一个旧金山的富二代,棒球狂热粉丝,平时的工作是“棒球纪录片导演”,对,一个衣食无忧的吊儿郎当的公子哥。公子哥老大不小,所以一结婚就想要亚罗怀孕。亚罗再一次逞了强,对新婚丈夫说,不行,她不可以一边做学生一边当妈。“做母亲是长期奉献。女人必须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衡抉择。”
丈夫等了她三年,36岁那年她生了第一个孩子,38岁第二个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她的“平衡”开始向家庭倾斜,她现在是一位联邦律师,因为这份工作能让她不坐班,经常在家陪孩子。“等孩子们再长大一点,我希望能花更多时间在事业上。”—又一次,亚罗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逞强。
爱与失落与我穿的衣服
安迪取出一个箱子,里面是这些年来他收集下来的几十封奖学金感谢信,有的来自我的学姐,有的来自我的学妹。坐在一间陌生却友善的别墅里,忘掉目的去读这些遥远的信件,它们的相似度让我震惊:它们都一律很长,一律都带着絮絮叨叨的小孩子气,一律都说到了选课和课外社团和暑假计划,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课表和社团活动,甚至选的课和参加的社团都差不多。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信一律都说,我非常喜欢这所大学,我适应得很好,我非常感谢你,就和我当初写得一样。我猜想,有多少个和我一样撒了谎,一边在为大学焦虑一边给凯恩太太装出了个笑脸。
138位女朋友,138位温柔善良的大一新生。
其中的一封信让人眼前一亮:在毕业两年之后,斯里兰卡姑娘奴雪突然又写了一封感谢信。和她大一寄出的那封信一样,这一封也是单向的信,一个人在汇报自己的生活而不求反馈。正因为其单向,里面昂扬的热情让人吃惊。她写,大学毕业之后,她本想做一个建筑师。回到斯里兰卡在城市规划局干了一阵子,她突然想起了自己的戏剧梦,于是两年内她在斯里兰卡乡村搭了一个儿童戏台,教学生学戏剧,学生是两个因为内战而敌对的少数族裔的小孩。
她写,在乡村戏台,她又想起了高三的时候收到的普林斯顿招生手册,册子里介绍校园建筑里的滴水嘴兽,那几段话深深打动了她。现在她想通了,她其实不想做那个搭造建筑的人,而是要做那个写作建筑的人,所以,她又要回学校读书了。她告诉凯恩太太,再过几周,她就要去波士顿读理论建筑博士。
所以,除我之外,另外一个对这个奖学金念念不忘的女孩子,居然也在波士顿。
我抬头看安迪,“如果彼得没有死,他大概永远不会认识一个斯里兰卡姑娘,也不会收到他的长信。”我突然这么一说。
安迪沉默了一会,“三兄弟当中,彼得是最国际化的一个。”
我看看窗外,康州格林尼治,一个非常富有又非常白的社区。
安迪说,“你说得对。”

波士顿4月的大雨,咖啡馆。奴雪湿淋淋地赶到,一个惊人美丽的短发姑娘,短发于她的效果就像赫本,一种似乎自己也没有预料到的果敢,奔涌而出的朝气。
整个一小时,我试图问她,斯里兰卡是不是有男女平等问题,在普林斯顿有没有受过性别歧视,有没有自己参与过女权运动。她苦思冥想,然后回答,没有,没有,没有。她说,“我不参加也不关心女权运动。”她的小学到高中都是在斯里兰卡的一所教会女校,我想让她讲讲女校的局限性,她却说,她们学校特别鼓励女生全面发展,不应试教育,不强调女性气质。这所女校出了好多游泳国家队运动员。
没有问到我想要听的“女性问题”,多少有些失望。
我看看表,和朋友的晚餐就约在隔壁的餐厅,还有五分钟。
奴雪看看表,离她下一班回学校的巴士还有五分钟。
为了消磨最后五分钟,我们闲聊。“你暑假干嘛?”
“我会回斯里兰卡,演一个话剧。好久没有演戏了,真兴奋。”
“什么戏?”
“叫《爱与失落与我穿的衣服》。你听说过吗?和《西雅图不眠夜》是同一个编剧。讲的是女人在不同场合不同处境穿什么衣服,不过,不是讲衣着的,而是通过衣着来讲女人对身份的认知。”
听上去真酷。
“有点像《阴道独白》。而且,全部都是女演员!”
“全部都是女演员?这是你第一次参加全体女演员的戏吧!”
“不是啊,我本科参加一个朋友的毕业戏剧作品,演的是一个不断变形的怪物,所以每一场都演一个不同的变形。这一部戏也有点女权,讲的是女性的角色转换。”
“等等,你跟我讲了一小时你不参加也不关心女权运动,现在却告诉我你一直在演这种全是女演员讲女权的话剧?”
她自己也吃了一惊,“说来也是。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想过呢?”然后她显得更不好意思了,“也许对我来说太自然了,反而没有想到。我更喜欢行动,而不是站队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正说到这里,她瞥到了窗外正驶过来的巴士,叫了声“不好”,一个健步奔向了公交车站,一头轻盈的鹿。
奴雪说,大学每年的学费相当于斯里兰卡当地货币五十万,她平生没看到过这么多钱。娜奥上大学那年,她的妈妈还在攻读博士,爸爸是一位工资很低的助理教授,她被五所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给奖学金最多的学校。莎拉说,普林斯顿的奖学金算法对农民家庭更优惠,她爸爸没读大学这个因素也让她拿到了更多的奖学金,她去普林斯顿比去耶鲁要每年少付一万美元。玛格丽特说,如果不是这个奖学金,她计划在麦当劳打工几个夏天,然后支付州立大学的廉价学费。亚罗说,她当时年纪太小,没担心过大学学费,直到她看到账单,毕业之后她花了十年,才还清贷款。所有这些女人都在大学期间打过工,很多人一周打二十个小时工,大多数是在食堂:早上四点切水果,晚上9点烤比萨。
如果不是彼得的奖学金,她们不会来到普林斯顿。其中一些人根本不会读大学。
彼得·凯恩的奖学金并不是全美唯一一个只给女生的奖学金。不过,与外界想象的相反,这一类专给女生的奖学金其实并不多,每一个的金额也并不丰厚,很多奖学金都有苛刻的附带条件。事实上呢,全美总金额最高的女性奖学金是Miss America,美国小姐选美比赛,每年给优胜者们提供总额为四百万美元的奖学金,条件是17岁到24岁女性,条件是从未结婚或者怀孕。条件是,你得穿着比基尼踩着高跟鞋在二十秒内回答“如何带来世界和平?”
《爱与失落与我穿的衣服》:我穿高跟鞋很漂亮。谁穿高跟鞋都漂亮。但是我脚痛。我的小脚趾总是被挤扁。我患了拇指囊肿。实在痛死我了,我不能思考。我必须选择——高跟鞋,还是思考。我选择思考。所以我买了些平底鞋。我犯了大错。商店里的销售员给我推销了这些绿松色的Marc Jocobs平底鞋,因为他说这些鞋能带来‘趾沟’。我从来没听说过‘趾沟’。无论如何,这些美美的平底鞋几乎和高跟鞋一样不舒服,对腿部也不好。幸运的是,就在这个当口,我认识了一个超级时尚的女人,她恰好只穿Birkenstocks平底凉鞋。我高中的时候只穿马丁靴,Birkenstocks平底凉鞋代表着一切我讨厌的东西。Birkenstocks看起来丑死了,穿这种鞋的女生会把自己丑陋肮脏的脚趾露在外面。我绝对不会和一个穿Birkenstocks的人成为朋友。但是呢,那个时尚女王把Birkenstocks凉鞋和一条喇叭裤和一件Comme de Garcons的无袖衬衫搭配在一起穿。这让我醍醐灌顶。第二天,我出门,涂了脚趾甲,买了双Birkenstocks:深棕色,传统样式。我明白了,Birkenstocks平底鞋其实是一个女人能穿的最酷最朋克的鞋子。它其实是一种宣言:“看吧,这是我的脚,人人都有脚,行了吧?”我丈夫却有不同见解。他讨厌我的Birkenstocks。他说这双鞋让我看着像一个从中土来的丑陋山精。有一回纽约洋基队进入了附加赛,他要求我换双鞋子再进客厅,省得我给洋基队带来厄运。我们离婚之后,你猜我会继续穿Birkenstocks,对吧?你错了。我又开始穿高跟鞋了。啊,痛死我了,我不能思考。我必须选择——高跟鞋,还是思考。我选择高跟鞋。”
(载于Esquire《时尚先生》2015年8月号)
后记:本文根据2015年春夏对于Andy Cahn, Sarah Wiley, Margaret Benefiel, Nushelle de Silva, Robin Stedman, Yaromil Ralph, Naomi Darling, Monica Dimitracopoulos, 和Connie Chan的采访。
如果一个人生命的开头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会是她人生唯一的一个故事。
现在,故事讲完了。写作这篇极度私人化的长报道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疲惫,让一个人直面自己的过去,一段永远无法消解的过去,是多么困难。我想,我再也写不了非虚构了,也再也没有理由去写非虚构了。那就把人生的最后一篇非虚构当作这个微信公号的开头。好多年之前,我在Wordpress上有一个博客叫“西西弗斯的健忘症”,后来这个博客被墙了,我转到还叫作校内网的人人网,后来人人网没有人玩了,我转去豆瓣,现在似乎豆瓣也没有什么人气了,就开个微信公众号吧。转来转去,只是希望有个发布文字的地方,不表演,不浮躁。一个旧博客,在微信时代试图重生。以后就主要在这里写字了,什么都写一点,小说、随笔、翻译。欢迎朋友们关注这个号lilyshen_blog。
原创内容,长按二维码识别,打赏10元。欢迎投喂。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