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翻译:玑衡
这个星期硅谷最大的新闻当然是Susan Fowler石破天惊的博文《反思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博文中讲了她自己作为码农入职Uber的第一天就被顶头上司约炮,向HR申诉结果被告知顶头上司是初犯,顶多口头警告。然而过了几个月之后她从其他女同事那里了解此上司精虫上脑,经常向同事约炮,每次都被HR告知是初犯……2/19号这篇博文发表后,事件迅速发酵,一天后,Uber就雇了前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介入,做独立调查。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自己曾经在美国职场遭遇过类似情况,申诉给HR之后,也是困难重重,无法惩罚当事人。
然而更严重的情况是……中国职场似乎还远未开始深度讨论性别歧视、性骚扰的问题。我在国内工作的几个月,各种性别歧视、骚扰、侮辱性话语天天不断,这样的情况在男性为主的创业圈更甚。因为这样的行为还未被定义,还未被“命名”,人人处在侮辱和被侮辱的角色里,无法自拔。
继续推送《硅谷故事》的连载,这是连载的第三篇。第一篇和第二篇分别在这里和这里。这几个小故事中也有讲到硅谷科技圈的性别歧视问题。原作:Anna Wiener , Uncanny Valley, N+1, Issue 25, Spring 2016 Slow Burn,翻译:玑衡。
另外,在后台看到很多祝福的话。最近两个月的确非常艰难,感谢大家的安慰和支持。
十一月凛冽的早晨,我司在101号公路上的广告牌揭幕了。那时候我加入公司才几个月,那天人人都早早地来上班,办公室经理给大家定了鲜榨橙汁、糕点、加了麦片的酸奶杯……我们集体出游,一起去广告牌。同事们一窝蜂地走过去,手插在口袋里,然后在广告牌前拍了集体照。我把照片转发给了在纽约的父母。照片上,我们手挽着手,自豪地微笑着。公司那个时候还很小,才三十来个人,一年之后我们有了一百多个人,再之后不久,我就离职了。
……
我和公司的一个销售一起吃午饭,我很喜欢他,他很好说话——因为“很好说话”是他的工作。我们在一个公园里坐下来吃着硕大的塞得满满的三明治,看着过往的游客。
“所以你是为啥选择了咱们的公司?”我问他。一块烤火鸡肉从我的三明治里掉到草地上。
“这还不容易么,现在硅谷都是一群二十几岁的小屁孩统领天下,这样的好事多久才发生一次?”
我决定“向前一步”,挑战性别定势,于是后来和这位男销售一起去了一场大数据的讲座。台上是两个搞风投的,穿得一模一样,这两人都异常能出汗,我坐在最后一排都能感觉到空气中潮湿的汗水。我此生从未去过一个房间里有那么少的女人、那么多的钱、那么多人想要挤进这个风口。这就好像看两台ATM机在讲话。我对我的男销售朋友悄悄说,“我想要专门研究男人是怎么看其他男人看大数据的大数据。”当然,他忽略了我。
我回到公司里,走进女厕所,看见一个女同事正弯腰俯身在水池前面,用纸巾擦脸。公司里没多少女的,我已经陆续撞见过每个女同事在厕所里哭。“我就希望这一切都能值。”她朝我这个方向吐了一句。我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当然是钱——但是我也知道她有多少公司股票,我也知道即使在最好情况下,她的股票也不值得她现在经历的这些遭遇。但是,在我能想出什么安慰她的话之前,她已经走出厕所回到她的办公桌了。
最近几天,我听到的所有谈话都是关于钱的,但是没人想要谈论具体数目。务必只在理论层面谈钱,人人有责。
我一朋友的室友赢了某公司赞助的Hackathon,于是在某个阴雨的周日下午他拿到了50万美元的奖金(其实是一百万美元,但是谁会相信我呢)。那个晚上他们在自家的双联别墅里面搞了个挺Burning Man风格的party:笑气罐、彩绘脸、设计精美的笑气烟斗——还有,靠着厕所门横陈着那张塑料泡沫支票。

在阳台上的简易冷柜边,我偶遇了另一个朋友,他在一家做云技术的公司工作,公司刚刚被收购。我开玩笑说这里是亿万富翁高帅富的俱乐部,他笑得像匹马似的,好像我讲的并不是个笑话似的。我从来没见他这样过,不过我也从来没见过刚得彩票的人,那种全身心都沉浸在自己的好运气里的人。他用自己打火机的棱角开了瓶啤酒,然后邀请我坐他的新敞篷车开去Mendocino兜风。是啊,天下掉下横财之后你除了兜风还能干啥呢。 “不过你知道谁是真正的赢家么?”他问我,然后马上讲了一个共同熟人的名字,那是一个聪明内向的码农,是公司的第一个工程师,很有可能是最核心成员。“秒成百万富翁啊,”我朋友仍然显得难以置信,好像刚刚那话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似的。“至少是八位数。”
“Wow,”我附和着,把我的啤酒递给他开,“你觉得他会想用这钱干啥?”
我朋友熟练地把瓶盖撬开了,看着我,耸耸肩。“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啊,”他用打火机敲敲自己的啤酒瓶。“我觉得他啥都不想干。”
……
高中老同学突然发了封email,介绍我认识他大学一哥们:一个新搬来湾区的码农。“没问题啊!”码农和我约定一起喝一杯,不过我不是很明白咱们到底是去约会的还是去搞人脉关系。其实两者区别不大,我有个朋友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呢:她总是去各种networking活动,心里明白无数去业界大会的人其实是去约炮的。一想到禁烟标间是公司信用卡付的钱,这批人就能硬得不行。言归正传,我的码农date很帅,危襟正坐,显得很甜。他看着像是一个对字体字号会斤斤计较的人,后来发现他的确如此。从见面一开始,就挺明显我们是聚在一起谈工作的。我们去了Tenderloin区的一个小小的鸡尾酒吧,有花色的墙纸和一个皮包骨头的保安。酒吧禁止拍照,也就是其实是故意怂恿大家偷偷拍照再发到社交媒体上。这个城市的精神变了,我很恶心自己居然亦步亦趋着这样的变化。
“这家店没酒单,也就是说,你不能随口说,你要个马天尼。”码农解释说,好像我正要点马天尼似的。“你得告诉酒保三个形容词,他会根据你说的给你调一杯。多好。多有创意!我一整天都在想我的三个形容词啊。”
怎样才算好玩呢?怎样才能感觉是赢了这个游戏呢?我试图投机取巧,要了一杯“烟雾的”、“咸的”、“生气的”饮料,暗暗期盼拿到的是一杯梅斯卡尔龙舌兰,结果果然如此。我们靠在墙边酌饮。码农跟我讲他在Mission区的复式公寓,他的特制自行车,他周中晚上要去露营旅行他有多兴奋。我们又聊了聊照相机和书。我们讲起我们都从未去过的城市。我告诉码农我的同事们都开始用一个个人形象设计服务,结果三个男的穿着同一件毛衣来上班,码农听着也笑了不过看起来有点惭愧。码农非常甜, 对自己的智商显得有点害羞,我想我们大概再也不会见面了吧。但是,那天晚上我回家后,感觉心中有很小很小的一块,被托起来了。
……
风投这一行最近几十年的创新可谓是开天辟地,比方说他们孵化出了这一代人最差的写作风格。整个互联网上尽是盲目自大而又了无经验的人在给彼此灌毒鸡汤:要么是个人轶事总结出来的教训,要么是简化为两三点的人生经验。比如这些:
你在课堂上学不到的十堂重要创业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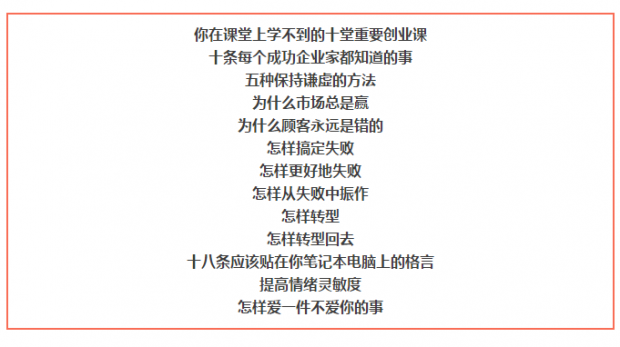
有时候感觉上去就是每个人都在讲不同的语言——或者说,虽然是同一种语言,却依循着截然不同的法则。我们公司全员会议的时候,领导给我们加油鼓劲。我们的主管看起来几天没合眼了,但是他仍然坐直了,眼神扫射着一张张面孔,和桌边的所有人做着直接而且精确的眼神交流。“我们的产品会推进人类的进步,”他是这么开场的。
社交狂同事在浏览一个大家自觉晒简历的网站,我偷偷在一边围观。他点开一个码农的页面,那个码农在一家嚣张又强势的创业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极速扩张、对市场控制权的无情追求、对道德边界的忽视都把我吓到了。在这家公司下面,码农这样写他的工作简介:这是艘火箭,亲,快上船吧。
我在等火车的时候注意到了一条广告,广告贴在站台靠近电梯的位置。做广告的产品是一个存密码的app,但是这条广告不是针对用户的,而是针对求职者的。是啊,这是投放给我的广告。广告上五个人站成V字形,双手交叉。他们都穿着一模一样的蓝色套头衫,戴着一模一样的橡胶的独角兽面具,我的脚正好踏在其中一个独角兽面具的。广告上这么写,“人类制造,独角兽使用。”
……
咱们雇了一个刚从顶尖大学毕业的女码农。她自信地走进办公室,春风拂面,充满热情。我们都期盼已久,终于有一个女性加入了我们的工程师团队。这对我们来说可是件大事。她的onboarding buddy带着她在办公室里转悠介绍,当他们走近我们坐的角落时,同事凑近我,手掌盖在我耳朵边说悄悄话:好像我们在搞啥阴谋,好像我们就五岁大似的。“这下糟糕,”他这么说着,湿乎乎的呼气撞到我脖子上,“我觉得每个码农都会爱上她的。”
我把这件事写进了给妈妈的email里。年终评定快到了,我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些对女同事有意无意的不友好行为写进年终报告里,这些行为给工作场合带来了不请自来的尴尬。我告诉我妈我有个同事的智能手表app就是一个GIF动画,一对永远跳个不停的胸;我告诉她我时常听到关于我体重、嘴唇、衣着、性生活的闲言碎语;我告诉她我们的第一个女码农恰恰是唯一一个没有SSH权限的工程师。我告诉她,和其他女同事比较起来,我在这里还适应不错,但这是因为我标准比较低。其实挺两难的:我喜欢我的同事们——我也常常开玩笑似地还击他们的话——但是,就用我们这一行的行话来说吧,他们这种歧视女性的举动是非常容易“规模化的”。我还没碰到什么真正恐怖的事情,不过我希望以后也碰不到这些事。我期待我妈会回复我以支持和鼓励。我期待她说,“宝贝真棒!你会给这一行带来改变的。”我妈收到email马上回复我了,“别抱怨性别歧视,除非你已经雇了律师。”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