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0
听报道
原作:Anna Wiener, Uncanny Valley, N+1, Issue 25, Spring 2016 Slow Burn
翻译:玑衡
为什么要翻译这篇文章?
好朋友是一个旧金山的产品狗,做了几年产品经理之后,他去了一家创业公司做产品总监。也就是说,那家公司目前只有他一个做产品的。某个周一的例会,公司在讨论一项工作进度,大家以颤抖的语气报告着种种“进步”和“好消息” ,却个个心知肚明这个进度已经严重拖后,没有可能按时完成。像第一次意识到“皇帝的新衣”的小孩那样,他向我宣布:我要换工作! 寻觅了一阵之后他找到了一家找不出缺点的独角兽公司,屁颠屁颠递简历,面试,却在最后一刻退缩了。问他撤销工作申请的原因,他翻开一本名字古怪叫作n+1的杂志,“喏,看看这家公司前员工写的。”
原文很长,很好,翻译的这几周来看哭了几回,因为篇幅的原因,准备分成四次连载,这是连载的第一篇。至于这家独角兽公司到底是啥,文末有彩蛋。 哦对了,文末的另一个彩蛋是!关于我的新书《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纽约的新书签售讨论会终于安排好了,时间是1月14日下午两点,这也是纽约文化沙龙2017年的第一场讲座,具体的报名方式在文末会详细写。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分享给海外党:《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的Kindle版本终于上架了,所以看不到实体版本的同学,快去亚马逊上下载电子版吧。
士气很低落。我们赚了很多钱,但是现在办公室里都是销售:衣冠楚楚的交际狗,举止得体,穿着高级皮鞋。当连不上VPN的时候,交际狗会轻声笑笑,抚顺头发。他们所占的办公室一角永远喧嚣,他们的桌上散落着来自其他创业公司的赠品:贴纸、杯套、U盘。我们不再参加公司团建的酒会和聚会。 “我们的文化正在死去。”我们沉重地说着,像末世预言。“我们该怎么救救公司文化?”
当然不止是销售。从来不只是销售。最近几个月,公司文化在慢慢瓦解。我们团队的核心成员被管理层推进会议室,质问他们的忠诚度。管理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海平面的变化,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心猿意马。我们不再去办公室内部的Happy Hour,不再用公款请新员工吃欢迎午餐。我们的KPI不再达标,也不再严肃对待OKR。同事不停地用这个词:恼火。我们的主要投资人投了我们的直接竞争对手。当然,这很正常,投资人们常这么做,但是这么做给我们的打击很直接:爸爸仍然爱我们,但是没有从前那么爱得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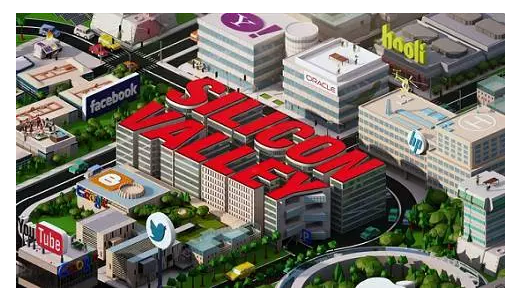
我们离开办公室,一起去了酒吧。当然,除了痛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共同点可以聊,然而我们总是一张口就开始猜测我们的工作是否会朝不保夕,抱怨大张旗鼓的官僚作风,指责工作中的障碍和错误的产品决定。我们说起IPO,好像那是从天上降下来拯救我们的神兵——比如IPO是不可避免的呀,比如我们现在拥有的股权就会把我们从存在主义的深渊中拉出来了,比如到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到这一股股集体恐慌了。说真的,我们都知道IPO有可能要等到几年之后了(如果真的会有IPO的话)。我们也发自内心地知道,有钱只是一个舒缓的膏药,不是解决办法。然而,我们仍然心存希望。我们自我安慰也彼此安慰:这只是一个阶段,每个创业公司都会经历成长的烦恼。最后,我们都会醉得不轻,醉到终于可以转换话题了,又重新想起了我们更加私密的自我了——那个我们在周末的自我,那个我们曾经的自我。
我们都是不公开的烟鬼,于是我们一起分了一包烟。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终于勉强承认了——我们其实非常在乎。我们非常在乎彼此。我们甚至非常在乎那些让我们感觉像屎一样的公司领导。我们希望领导们过得好,就像我们希望自己能过得好一样。我们在乎,真他妈操蛋,我们在乎公司文化。我们是公司的前二十个员工,我们在创造人们想要的东西。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工作已经深深刻入了我们的身份认同,唯一能够保持理智的方式是坚称,我们就是公司,公司就是我们。每当我们在健身房里看到一个陌生人穿着我们公司logo的T恤,每当我们的名字被社交媒体或者客户的博客提到,每当我们收到一个正面的客服反馈,我们都会在公司聊天室里贴出来分享,我们很自豪,真真切切地自豪。
但是我们现在算是看清楚了,我们此前一直在这碗公司煲的鸡汤中游泳,现在却不得不浮出水面。我们曾经幸运、有权有势,现在我们却沦为了一群官僚,在电脑前敲字,让另一些人——一群小屁孩!——富得流油。 我们把烟头扔在路边,用脚碾碎。打开手机叫完出租,我们猛灌下最后几口啤酒,手机屏幕上已经看到出租车的卡通图标离得很近了。我们散了,去吵醒熟睡中的室友或者伴侣,在睡前回复最后一两封邮件。 八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办公室,灌着咖啡,出去买黏嗒嗒的早餐三明治,调整着平庸的代码,写着违心的email,在办公桌的两侧交换着疲惫的互相理解的眼神。
我像看星座运程那样浏览招聘email和职位简介,一直下拉到员工福利:工资、牙医险、眼科险、401k养老金、免费健身房会员、免费食堂、自行车停车位、去Tahoe雪山的滑雪旅行、去Napa酒庄的“工作日”、去拉斯维加斯的“会议”、 无限啤酒、无限精酿啤酒、无限康普茶、红酒试饮、周三威士忌日、周五酒吧日、按摩日、瑜伽日、桌球、乒乓、乒乓机器人、玩具球池、游戏夜、电影夜、卡丁车、滑索飞行。职位简介是一个好地方,能了解HR心中的“娱乐”和23岁小屁孩眼里的“工作/生活平衡”。有些时候我读着读着就忘了,以为我在申请一个少儿夏令营。来,读读这条。人性化设计:利用最新硬件,自主设计你的办公空间。 改变你身边的世界。帮助人类繁荣,通过——好吧,看下一条:我们用力工作、用力笑、用力击掌祝贺。我们的码农在TopCoder评选出里名列前20。我们不只是另一个社交app。我们不只是另一个项目管理工具。我们 不只是另一个在线支付处理器。我出门去剪了个头发,继续看职位简介。
大部分创业公司的办公室看着都一样——仿20世纪中叶风格的家具、砖墙、零食吧、酒吧。硅谷的室内设计就两种类型,要么非常在乎自身品牌,要不非常文艺。当科技产品投射到现实世界,它们把审美趣味也投射到自身上,好像这样就能坚持着它们的存在:一个短租网站的办公室装修得像这个网站上各类房东的泳池别墅或者休假屋;一个做酒店预订的创业公司的前台没有前台小姐,反而装满了酒店式的电铃;一家叫车app的总部闪耀着和app相同的主题色,一直闪耀到电梯口。一个和图书有关的创业公司有一个又小又令人难过的图书馆,书架半空,软皮的小说书和基于对象的编程手册胡乱堆放在一起。这让我想起了,故意穿成Michael Jackson样子去参加Michael Jackson葬礼的人们。

不过,这间办公室——这家拥有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而且并没有靠谱收入模型的创业公司的办公室——实在是尤其性感。 基本上一个办公室不该有的,它都有了,这实在让我心跳加快,异常快。办公室里基本能看到城市任何一个方向的风景,地上放着肥肥的皮革双人沙发,电吉他插在扩音器里,柚木柜子,白色硬件。这看起来就像,我22岁的时候曾经幻想过的著名歌手男票的公寓。我真想脱下我的裙子和鞋子,躺在巨大的绵羊皮地毯上,吞下一巴掌的摇头丸,把身体弯进碗形的Eero Aarnio椅子里,再也不走了。
不是很明白我到底是来这里吃午饭还是面试的,当然这也很正常。这两件事情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我的着装两头都不搭。我的“向导”带我穿过公用厨房,里面基本有所有创业公司都有的零食储备:塑料桶里装着混合坚果和Goldfish零嘴,碗里放着薯片和小棒棒糖。当然还一定可以看到整箱整箱的Clif牌能量棒,冰箱里有果味的水饮料、乳酪棒、一人份巧克力牛奶。很难分清这家公司到底是在训练马拉松还是在吃课后零食。有一次我走进咱们的公用厨房,看到两个账户经理在狂吃Shot Bloks——乖乖,那是一种专门卖给耐力运动员的能量棒。
午餐是送货上门的阿富汗菜,我在午饭中见到了这个团队,其中包括一个亿万富翁,发迹的原因是他搞过一个让百姓能和名人套近乎的网站(虽然在现实中他们一定会讨厌这些名流)。亿万富翁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了他。“哦,”他把一块阿富汗饼掰成两半,并非不友好地回答说,“我知道你们公司。我曾经想过收购你们。”
今天我又一个理由也没给就请假了,我担心其中的挑衅成分太明显。 整个上午我都在喝咖啡,不停浏览科技新闻,然后整个下午我进城里参加面试,对方是一家和花生差不多大的创业公司。所有的面试官都是男人,这没啥问题。我喜欢男人。我有过一个男朋友,我还有一个哥哥。男人们问我这些问题,“你怎么计算有多少人在美国邮政系统工作?”“你怎么给一个中世纪农民解释互联网?”“你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是啥?”他们叫我站在一块白板前面图解我的回答。这些傻问题本该让人生气、感到冒犯,但是却让我兴奋、充满干劲。我想要让人印象深刻,我不会被这些自视过高的问题挫败。我觉得这是我的性格缺陷,也是为什么我进入科技这一行的原因:我真他妈百折不饶,对于负面的东西,我总是在积极应对。
我的第三个面试是和这家公司的技术联合创始人。他进入会议室,穿着一件干练的蓝色衬衣,看起来充满自信地毫无准备。他用抱歉的语气告诉我他没有面过很多人,所以他没有多少问题可以问我。即使如此,办公司日常经理仍然定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聊天。我觉得没有大碍:我猜我们总可以聊聊这个公司,我可以问一下常见的问题,然后熬到四点我就可以结束这一天,就像一个放学的中学生,然后这个大都市就会重新接纳我和我犯下的傻。可是,联合创始人告诉我,他的女朋友在申请法学院,他在帮她备考。所以,他不想给我一个寻常的面试,他准备让我做一套LSAT模拟卷……我搜索他脸上的表情,希望能看出他其实在讲冷笑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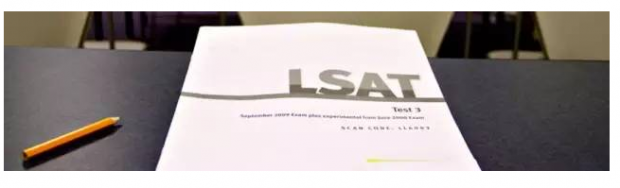
“如果你不反对,我就准备留在这个房间查查我的email,”联合创始人这么说,把试卷推到桌子的我这一边,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他按下了闹钟。
我提前完成了试卷,我一直都个学霸。我检查了两遍。联合创始人当场批改了我的答案。“我妈一定会为我感到好骄傲的,”我开着玩笑, 感到非常聪明非常错位非常低落,比低落更低落。
家永远是我的避难所,不过有时候也不是这样。我的室友要三十岁了,为了庆祝她生日我们在公寓里办了一场葡萄酒奶酪派对。好吧,其实是她办派对——我是被邀请的。她的朋友们准点到达,穿着商务休闲装。她招待客人吃几百块钱的奶酪,“Bi-Rite买的,当然啦。” 她穿着黑丝绸面料,看上去很优雅,边说边在饼干上抹着Humboldt Fog奶酪。我室友在西湾的半岛上工作,公司是一个大家都讨厌却不可能不用的网站。我们在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在创业者的世界,永远小屁孩的乐土;她却已经是一个大人了,像所有其他的大人一样,在一家大企业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扮演自己的角色,为自己的地位斤斤计较。我崇拜她却不理解她;我猜她也许觉得其实我挺好玩的。大部分时候,我们只讨论健身。

古典音乐在室内悠扬播放,有人打开了一瓶得体的香槟,并且反复告诉大家这的确是法国产的,当香槟的瓶塞崩开时,大家鼓掌。我室友和我一样大,但是我感觉是置身在我父母的派对上,我立即感到了嫉妒、非常想家。我回到自己的卧室,锁上门,换上了一条紧身晚裙。每天吃坚果零食,我已经胖了十五磅:吃的时候感觉不像吃了正餐,但是长此以往,身体就显山露水了。当我重新回到客厅的时候,我吸紧肚子,在人群的背后穿梭,希望能找到一群人聊天。在沙发上,一个穿西装夹克衫的男人正在夸夸其谈“大麻生意的机会”。所有人都看着很自如,没人想和我说话。他们把葡萄酒杯倾斜在合适的角度,他们优雅地掸去手掌心上的面包屑。我听到的最常见的单词是收益。哦,不对,是策略。我无事可做,只能喝酒,沉溺于自我。我跟着这群陌生人去了公寓楼的屋顶,感觉到自己正在刻骨铭心地想妈妈。在远处我能看到Castro大街上那面著名的彩虹旗,旗帜的边缘不停地在空中鞭打。
“看,那里是奥克兰,”甲这么说,“我们会在那里投资的。”
“那块太危险了,”乙这么说,“我老婆从不去那里。”
“当然不去,”甲这么回答,“买得起房的人都不住在那里。”
等到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我换上套头衫和底裤,毫无效率地开始打扫:舀起奶酪渣子,冲洗塑料杯,用湿手捡起巧克力蛋糕……我的室友走过来说晚安,她看起来美极了:微醺,因为全世界带来的善意而光芒四射。她和她男票回到了他们的卧室,我在走道的尽头听到他们安静地更衣、上床、进入好梦。

和这个树洞讲讲你的创业故事吧
这就是原文连载的第一部分了,原文过长,准备分四次推送给大家。本文的原作者Anna Wiener曾经是Mixpanel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些故事是她和公司多位同事聊天的产物。这些故事真实得令人害怕,这让我想起了我朋友们的生活,我自己的生活。Mixpanel这家公司也许不算尽人皆知,因为它的产品是2B的,为其他公司提供商业数据的分析。 公司创立近八年了,已经是独角兽也有一会儿了, 2014年公司寻求融资的时候,估值已经达到了九亿美元。 Mixpanel到底碰到了什么问题呢?CEO非常年轻,大学没毕业就创业做了这公司,今年仍然只有28岁,缺乏各类经验。IPO本来无限接近,现在却显得遥遥无期。因为管理层的经验缺乏,公司人才流失严重,业务拓展也碰到了问题。 总之,一个创业公司可能想象到的问题,Mixpanel都碰到了。
查了查作者Anna Wiener,她的生活方式让我着迷。她是一个很严肃的作者,作品大多是非常真实的讲述创业者生活的文学作品,散见于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这样的顶级杂志。而她平时的全职工作是各类技术工作中的后台人员,工作更换的频率很高。可以想见,在这一份份全职工作中,她实际上在做的是“人类观察家”,故事听够了,人看过了,就把故事和人写到“小说”里,然后走人,换下一份工作。态度潇洒,不卑不亢,令人羡慕。
所以,你也在创业公司工作吗?你也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吗?有什么创业故事不吐不快又担心得罪老板? 在这篇文章下面留言,注明“私密”, 告诉这个树洞吧。如果集齐了足够多的故事,我会编辑一下,隐去所有可能猜出隐私的部分,结集发一篇来自读者的创业故事们。
1月14日纽约文化沙龙见
虽然淘宝的海外集运功能很不好用,但是的确在无数条“亲,怎么又出问题了”之后,拿到了DHL的快递号,几十本《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的实体书已经在飘洋过海到纽约的路上了。
虽然一月份大学的教室纷纷关门了,“纽约文化沙龙”仍然在曼哈顿找到了很合适的场地。深深感激组织者赵智沉。
虽然那可老师在跑完七大洲和北冰洋马拉松之后,仍然一刻不歇在各地跑步,然而1月14日下午,他的确会来做这场活动的嘉宾。
是的,2017年1月14日下午两点,纽约文化沙龙,我的新书《中国特色的译文读者》会举办一场讨论和签售会。地址是Alchemical Studios, 104 W 14th St, New York, NY 10011
纽约文化沙龙的活动很火爆,所以需要提前报名。具体的报名入口会在活动之前两周左右公开,请大家提前关注纽约文化沙龙的微信号(nyshalong)或者网站()。
纽约见啦。
文章原题为:硅谷故事:唯一能够保持理智的方式是坚称,我们就是公司,公司就是我们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